
2014年莫迪政府高调推出 “印度制造” 计划股票配资持仓,目标是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%并创造1亿就业岗位。
然而十年间,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,从2014年的16.5%跌至 2024年的14.1%,2025年更降至约13%。
这一倒退折射出印度工业化进程的深层困境:即便投入230亿美元的 “生产关联激励计划”(PLI),最终也因执行低效、补贴发放缓慢而宣告失败,仅完成目标产值的37%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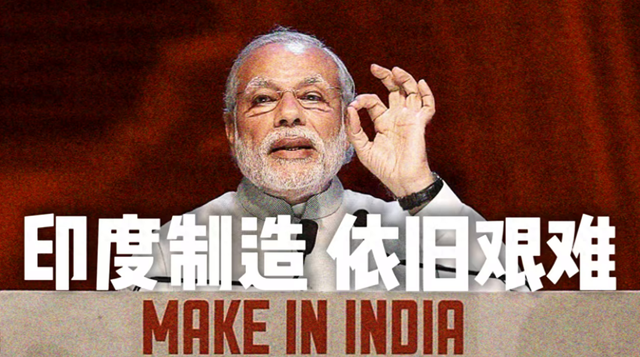

印度制造业的核心矛盾在于产业基础薄弱与战略野心的撕裂。以电子产业为例,尽管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,但70%的炼钢设备、60%的电子元件仍依赖中国进口,本土零部件本土化率仅35%。
这种 “组装依赖” 导致每部iPhone在印度的获利不足25美元,而苹果公司在美国的单部利润超过450美元。
更讽刺的是,印度为削弱中国供应链,对进口零部件加征关税,反而推高本土企业成本 —— 手机零部件采购成本因此增加40%,进一步削弱竞争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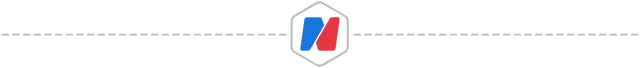
印度工业化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土地私有制引发的治理僵局。2017年启动的孟买 - 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,原计划2022年通车,至今仅完成10公里建设,工期推迟至2028年。
问题根源在于508公里线路途经大量世袭地主土地,政府无法强制征收,只能逐户协商。这种 “一户否决权” 导致项目陷入马拉松式谈判,而地主阶层通过土地垄断将约2.6亿劳动力束缚在低效农业中,形成 “工业化缺人、农业内卷” 的死循环。

更深层矛盾在于国家权威的结构性缺失。印度通过 “非暴力不合作” 建国的路径,使其统治阶层缺乏集中资源的能力。
地方势力为维护土地利益,常以 “吃拿卡要” 阻碍政策落地,甚至出现 “政令不出新德里” 的荒诞局面。
这种治理困境不仅拖慢基建,更导致佃农权益严重受损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圈地运动释放劳动力的经验,在印度因制度性障碍难以复制。

印度虽拥有14亿人口,但人力资源质量与制造业需求严重脱节。2022年数据显示,三年级学生仅能认读一年级文本,六年级学生中40%无法完成简单除法。
教师资源匮乏、政策落实不力,使得扫盲教育沦为形式 —— 印度将 “会写自己名字” 定义为 “识字”,这种自欺欺人的标准导致劳动力技能普遍低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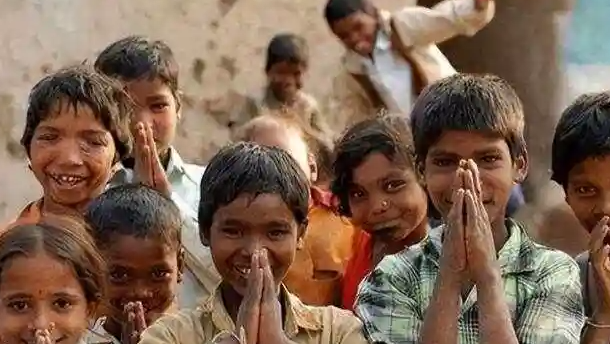
更关键的是,教育方向与产业需求错位:本应在初级阶段发展职业技术教育,却将资源投向精英教育,培养的人才大量涌入软件业,2025年软件业占GDP比重达10%,形成 “高端服务业虚火旺盛,制造业人才空心化” 的畸形结构。
这种教育断层直接削弱制造业竞争力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,印度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6.5年,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超70%,而制造业需要的纪律性、标准化工人严重短缺。
更严峻的是,2020年后,约6000万劳动力从城市回流农村,农业就业人口回升至2.6亿,进一步抽空制造业劳动力池。


印度的工业化困境不仅源于内部矛盾,更因地缘战略的根本性失误。
2019年莫迪政府退出RCEP(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),主动放弃融入包含日韩高端产业、东南亚劳动力的区域经济圈,导致与东盟贸易成本比中国高18%,丧失产业链整合机遇。
转而投靠美日澳印 “四方机制”,试图通过配合美国 “去中国化” 获取技术转移,却发现美国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对印投资仅占对华投资的3%,沦为 “战略棋子”。

更致命的是,印度将工业化希望寄托于中美对抗的 “窗口期”。2020年边境冲突后,印度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、打压中企,甚至协助菲律宾在南海挑衅,试图向美国表忠心。
然而随着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取得突破,原本流向印度的制造业投资出现 “停滞或回流”,苹果等企业的供应链转移计划因中国成本优势难以持续。
2025年印巴冲突中,印度虽宣称 “胜利”,却暴露空战体系落后,彻底失去美国扶持价值,其 “世界工厂” 梦想终成泡影。

印度制造业的十年倒退,是制度缺陷、教育断层、战略短视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当中国通过产业集群、高效治理实现 “产品迭代 — 技术升级” 的良性循环时,印度却因土地垄断、政策摇摆、路径依赖陷入 “低端做不好、高端做不了” 的困境。

更可悲的是,其地缘投机不仅未能换来产业链转移,反而加剧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——2024年对中国贸易逆差达992亿美元,进口以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为主,制造业整体陷入亏损。
“人和不行、地利不在、天时不占” 的印度股票配资持仓,在工业化赛道上已远远落后于时代。
尚竞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